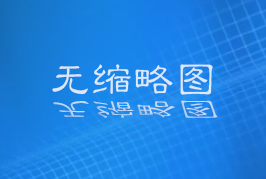6月11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关于避免人才项目异化使用的公开信(下简称“《公开信》”),刷遍了科学界的朋友圈。
基金委《公开信》中批评人才项目被异化为“头衔”和“荣誉”的现象,并声明人才项目旨在支持项目负责人开展基础研究工作,并在一定期限内完成科研任务,而非荣誉称号。
《公开信》还指出:人才项目之原意,并非为负责人贴上“永久”标签,科技界应关注负责人在资助后的进步。基金委鼓励有关部门和单位,设置更全面的人才评估标准。
中国科技界的“帽子满天飞”问题,近年来频频遭遇诟病,《知识分子》此前多次发表评论和专家讨论文章,切中肯綮,引起广泛关注。值得注意的是,此番国家自然基金委的表态之前,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在两院院士大会上也多次谈到科技界的人才问题——“项目多、帽子多、牌子多”等现象仍较突出;人才评价制度不合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的现象仍然严重,名目繁多的评审评价让科技工作者应接不暇,人才“帽子”满天飞……要通过改革,改变以静态评价结果给人才贴上“永久牌”标签的做法……
显然,“帽子问题”凸显了人才管理制度不适应科技创新需求,不符合科技创新规律,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率先表态,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改革的先声。《知识分子》邀请到几位科学界人士,再次聚焦人才的“帽子”问题。
“帽子”带来的问题
“帽子”问题的实质是人才评价和科技资源分配问题,反映在科学界最容易被人诟病的地方在于,“帽子”一旦戴上,极易产生赢家通吃的效果。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星系宇宙学部副主任、”百人计划”项目负责人雷提到,现在评项目往往是把不同学科,或者不同学科的不同方向放在一起混着评,导致评审的专家实际上是外行。由于不同学科的差别极大,不能数论文,所以最后就数“帽子”。“一直都是这样执行下来,就不会有人去考虑如何更准确地评审。”雷说。
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谢宇也提到关于“帽子”的其他一些问题。一是这些头衔更多是来自官方,而非学术共同体承认。第二,“帽子”偏爱受过国外博士后训练,以及评审中往往有对年龄的限制,其实是歧视的一种。“我们应该鼓励在工作中抛弃年龄、学历、居住地,自由公平竞争岗位。”谢宇说。第三,有的学者在获得“帽子”之后,因为“帽子”所带来的一些“特权”,不再或较少受到约束,甚至不产出、造假,却没受到惩罚、被追究责任。
“帽子”的合理与不合理
广东某大学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行政管理者向《知识分子》表示,他从公开信中看到,基金委明确了资助的目标是项目本身,而不是负责人;人才称号不是永久标签,而是阶段性考核。“这是合理化的进步。对我们科研工作者来说也是更公平的,也是更有激励性的”,他说。
“发这样的公开信出发点是好的,但更期望基金委自己从此以身作则。”原上海科技大学教授、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电子工程与计算机系教授马毅说。马毅认为,现在“帽子”如此重要,主要是因为没有“帽子”的人,无法凭能力拿到重要的科研项目。如果评项目是靠能力,那“帽子”自然不会那么重要,大家也不会去争“帽子”了。“任何好的制度和标准的建立,主管部门自己必须以身作则。”他强调说。
谢宇也表示:“帽子”在人类社会构成中不可避免,对政府的管理和决策也非常重要。他解释道:当社会规模越来越大,我们便没有时间去充分了解某一个人,此时就要依靠名誉、头衔这样的线索来推断关于某人的信息。“帽子”毕竟也是经过专家评审,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公正性,管理者们更是需要这些线索来辅助决策。同时,以“帽子”引才,成了高校看得见的政绩,比如学科评估、申请项目等等都需要看“帽子”,某种程度上,“帽子”成了机构学术能力的表征,由此导致各类考核考评中数“帽子”的简单化做法。
谢宇也强调,要警惕对这些线索的滥用:“帽子”在统计学上有意义,但不能精准地反映个人的能力和贡献。因此,对个人的评估手段必须多元化。
香港科技大学物理系教授、原中科院物理所”百人计划”入选者戴希,也认为目前人才评估标准单一。他表示,中国大学教授的待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普遍偏低,为了吸引国外人才回归,也为留住自己培养的部分优秀人才,必须给予少数人特殊待遇。“但如何公平地鉴定谁是人才呢?这些国家层面上评选出来的帽子们,就成为天然存在的客观标准”,戴希说道,“但问题是,用全国统一的标尺去衡量不同学科,不同地域和不同单位,也许可以做到客观,但很难做到合理。这对科技界内部生态多样性的建立也很不利。一个创新社会的建立,离不开这种多样性,千篇一律是创新的天敌。”
在科技界,有“帽子”的人往往资历较深,对于资源分配的话语权更大,而初出茅庐的青年科学家为了争取资源,不得不在追逐帽子的过程中,分散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往往成为受害者。
中国科学院大学卡弗里理论科学研究所所长张富春告诉《知识分子》,当前引进和激励青年人才的奖励政策有“四青”——中组部的青年千人计划、基金委的优秀青年、教育部的青年长江、以及万人计划中的青年拔尖人才——这些计划在过去一定时期都起了正面作用。现在来看,名目太多,挤占了青年学者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一位人大朋友告诉我,过去一年人大仅申请长江学者或青年长江学者就有90位,每位申请者平均花一个月的时间准备材料,结果是百分之十的人取得了荣誉。”张富春说,很多青年获得了青千,还要申请其他的人才计划,学校和研究所也鼓励他们再申请,因为学校视四青数目为学校质量的重要标准。
张富春对此感到可惜:建设创新型国家,应该大力鼓励创新,让年轻人集中精力创新,而不是花太多时间申请这些。
“帽子”问题如何改
广西大学校长赵跃宇此前在《知识分子》认为:“人才计划问题的异化看上去是帽子、票子、位子的问题,归根结底却是分配制度的问题。”
他认为,现在高校、研究院所的绩效薪酬制度既不适应高校、也不适应人才市场。同时,国家对机关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实行大一统的薪酬政策。高校、科研院所难以形成体现本行业特征和具有自我约束、自我调节的薪酬制度,这就迫使着“帽子”不断演变为位子、票子的砝码。
雷向《知识分子》表示,各种人才计划一开始都是以引进人才为目的实施的,现在国内研究水平会越来越好,我们就需要考虑这种针对部分学者的激励政策是否合理。“现在收入差距变得很大,低的非常低,高的非常高,而且收入高的还经常被挖来挖去,跳来跳去。”他说。
张富春也建议:把“四青”整合为“一青”,平等对待国内培养和海归青年人才。“青千计划总体是成功的,引进了成千上万名优秀学子从海外回国。但是这个政策把国内和海外的青年人才截然分开。我们有一些研究所、大学已经是国际水平了,拟应同等对待。”张富春说。
雷还提到,我们缺乏备用的评估标准。他说:“我们国家现在的特点就是管理权和经费都在管理部门手上。如果从长远来说,应该是逐渐淡化管理权限,把一些决策权下放到研究所或者是一些专门的科学家,比如说通过制定规划,成立学术委员会,通过这些方式来逐渐改善评估。当然,从目前来说,权力基本上都还是集中在政府层面。”
戴希也认为帽子问题的根源是体制上的。他认为主管部门对基层单位的各类评估和检查过于密集。这些活动导致了按照帽子大小和多少,来进行利益分配的格局。“不在根本上改变这一点,科技界的帽子问题就跟中小学生的减负问题一样,很难得到根治。”戴希说。
邸利会、李可对本文亦有贡献
作品来源:《知识分子》(微信公号:The-Intellectual)
《知识分子》是由饶毅、鲁白、谢宇三位学者创办的移动新媒体平台,致力于关注科学、人文、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