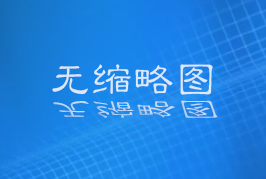照相

儿时,在奶奶身边看到二大爷从广州寄回来的照片,感到很神奇,一个大活人像画一样展现在一张纸片上。我什么时候也能照张相呢?
我的第一张照片是1955年冬天照的。父亲要从通辽调往呼和浩特工作,领着全家人在通辽的一个照相馆拍下合家欢。依稀记得一天下午,母亲给奶奶和我们几个孩子换上了新衣服,梳妆打扮一番,跟着父亲去了照相馆。摄影师傅把我们几人摆弄好后,让眼睛看着照相机,然后他把头埋进黑布里,屋子灯一下子都亮了,只听“啪”的一声,我吓了一跳,照片就照完了。照片洗印出来后,由于让眼睛盯着相机,我的眼睛瞪得圆圆的,哪像现在孩子那稚气、充满童趣的自然表情和姿态。
来到呼和浩特后,我们家住在内蒙古中医院家属宿舍。邻居是医院周秘书。当时他们夫妇没有小孩,挺喜欢我,我也帮他们干些力所能及的活。那时,周叔叔掌管单位照相机,节假日有时拿回家给人们照个相。他给我在人民公园、博物馆前照过相,相片都是他自己冲洗出来的。他告诉我,这个相机是德国蔡斯牌120双镜头,还有一种相机是135单镜头的。我对相机有了兴趣,他教给我什么是物镜、光镜,如何对光圈,调焦距等等。因为那时胶卷很贵,跟周叔叔学也就是他调好焦距我摁一下快门而已。
小学毕业,我们班十来个男生凑钱买了一卷胶卷,我从周叔叔那里借来照相机,在公园照了12张照片。洗出来后,照片上有人影,但还是曝光时长时短,或是焦距不准,效果不佳。以后,我又断断续续用借来的相机照过相,慢慢摸清了门道,照相技术有了提高。1968年8月,我到呼和浩特钢铁厂工作,几年后调到总厂政治部。领导把单位的照相机交与我保管。这是一台德国产的禄莱牌120双镜头照相机。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不但提高了照相水平,而且掌握了暗房技术。那时经常用给单位拍摄后剩下的胶片,给同事们、家人拍照,然后自己冲洗放大。我和爱人、孩子在呼市很多著名景点都留下了影像。两个儿子的百岁、一岁照,都是我亲自摄制、亲自冲洗,现在还保留着,很是珍贵。
学会照相后,我想拥有自己的一架照相机,但那时经济力量有限,家中有这个奢侈品的也是凤毛麟角。改革开放后,收入增加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买了一台日本产的傻瓜照相机,花了五六百元人民币。所谓“傻瓜”,就是不用对光圈、调焦距,只要把人物、景物放到取景框里按下快门即可。效果是相片层次感差。遇上节假日,带着老婆孩子逛公园,照上几张黑白照片。以后,兴起彩色胶卷,价钱较贵,也就量力而为了。
21世纪初,用胶卷的普通相机渐渐消失了,数码相机进入普通家庭。不用底片,影像可存入电脑,想洗印照片,把卡上的数据输入电脑即可打印出来。拥有相机不再是为了留影,而是为了创作。在一些景点,经常看到人们举着相机,对着一只鸟、一朵花、一泓碧水搞艺术享受。什么长镜头、广角镜头、单反等专业设备装满摄影包。少则五六万元、多则几十万元。特别是手机进入4G时代后,取代了普通相机,既可照相、也可录像,还可通过微信直接发到朋友圈里。照相机的神秘感、新鲜感在人们心中慢慢消失了。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放录机开始在中国出现,把它接到彩色电视机,人们可以欣赏到不少电视连续剧。谁搞到了录像带,就到处借放录机,然后呼朋唤友聚集一屋子人去看港台大片。于是就出现了陈佩斯、朱时茂小品里演的警察抓看黄色录像的故事。随后,家庭录像机进入有海外关系或首批万元户的家庭。办喜事的宴席上也开始用录像机记录热闹喜庆的场面。
2001年,我去广州开全国职教现场会。会后大会组织去深圳参观,有幸第一次到沙头角中英街。这条街两边商铺鳞次栉比,基本上都是服装鞋帽、化妆品、电子产品,价格比内地便宜三分之一甚至一半。我和同事进了一家专卖摄像机的商店,那里摆满各式各样各种品牌的摄像机,基本都是日本产的,有索尼、夏普、日立等。导购员非常热情,不断从货架上拿下摄像机给我们看,讲它的性能、效果等。我被说动了,当时就用6000元买下一台夏普的家用摄像机。本来出差时没有这项个人开支预算,原打算去昆明参观职业教育先进单位后,去西双版纳游玩,因钱袋空空,不得不提前打道回府。回来后,我照着说明书自学使用。一有空就带着出去摄录街道、行人、公园美景。
不长时间,大孙女诞生,我把摄像机给了大儿子,让他用摄像机记录孩子的成长过程。二孙女出生后,又用它摄录了她稚嫩天真的童年。我把录像带刻成碟,让他们父母保管起来,等她们成人后,这是一份多么珍贵的记录啊!
前几年,儿子给我买了一架卡式数码家庭摄像机,,能直接连电脑播放。我和老伴外出旅游都带着,摄录祖国壮美山河、旖旎风光。我们把这些都输入电脑,准备编辑成像,也是对日新月异的幸福生活的点赞吧!文/刘海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