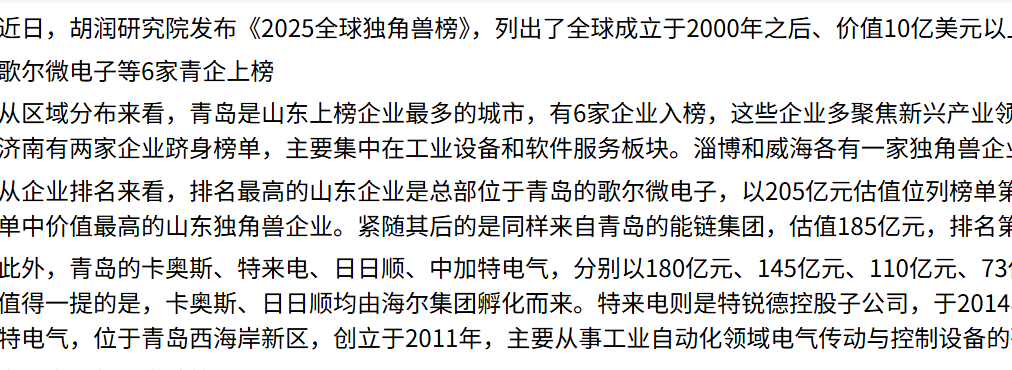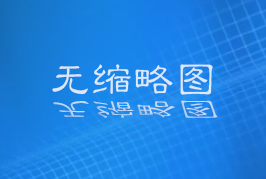(原标题:民国“黄金十年”的真实面相:农村陷入“总崩溃”)
以“黄金十年”来描述国民政府南京建政后十年间发展的历史,已经成为学界一种比较流行的表达。这种说法认为,这一时期中华民国在政治、经济、基建、文化、教育、社会政策、边疆民族政策、外交以及军政建设各方面均有新的取向和建树;但现代化工业的推进及其成就,无疑构成其所谓“黄金十年”的根基。经济史学者的研究提出,1912—1936年间,中国工业年增长率9.4%。仅就工业化或者现代化建设成就而言,“在抗战前达到了旧中国经济史上的最高峰”(王玉茹、刘佛丁、张东刚)。历史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演进,而是复杂的多面相的有机整体。拘执于一端,或可清晰勾勒或凸现其事体本末,但却常常以此而忽略或遮蔽另一端(或他端)的事体,从而难以获得全面而真实的历史认知。
“黄金十年”使中国工业“已具雏形”
近代以来,以现代化为指向的工业化进程的诉求始终构成民族复兴的主导取向,“我国机器工业,肇始于同光,建设于清季”(龚骏)。自1863年江南造船厂创设现代工业开始,工业化趋势奋然而成时代之潮流,“朝野上下,公认新式工业之提倡,乃救世匡时之上策。”(罗敦伟)
民国十年之建设既是晚清同光以来的历史延续,也有着新时代的努力和追求。肇始于清末的现代工业,“盖有八十年于斯矣。”国民政府提出八大政策要项(即提倡做工、振兴农业、鼓励垦荒、调节消费、振兴工业、开发矿产、流畅货运、调整金融),并成立国民经济建设总会,发起颇具声势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而及于工业建设之影响,较之过去任何时期,实为巨大。”仅就工业投资额而言,诚为世人所瞩目:“自民国十六年以来,七八年之内国人投资一种新工业资本超过百万元者,几如凤毛麟角,而二十四年以后,则百万元之工厂,乃至千万元之工厂,均甚多。如中央机器厂、中国酒精厂、永利公司铔厂,以及最近筹备之各工厂,资本即以千万元计。”时人评论此为“工业史之新局面,可以大书特书者也”。
确实,抗战前国民政府还拟定了三年重工业发展计划,如不发生战争,在可预期的七八年间,可望在钨矿、锑矿的开采和钢铁冶炼工业建设上取得成效,如“炼钨厂,每年出三十万吨优良之钢,可供中国一半之需。”(沈雷春、陈禾章)基于工业增长的事实及其数据,不难断定,民国建政直至抗战前夕,“我国工业可谓已具雏形”(洪丈里)。

“黄金十年”时的农村陷入“总崩溃”
现代工业的快速增长不过为其整体历史进程之一端,与现代工业增长态势相伴随的中国乡村却陷入严重而持续的危机之中。孙晓村、张锡昌以《一个农村经济崩溃的过程》作为《民元来我国之农村经济》的开篇之题,显然既不是故作危言耸听之论,也不像如今一些学者所言乃民国知识分子“普遍左倾化”的主观想象,而是基于一种基本史实的评判。
1934年《农情报告》(根据二十二省之调查)显示,中国农民的生活境遇较之于英、美、法农民平均数相差太远。“以如此狭小之耕地经营农业方式,虽极端节约,农民虽极端勤劳,而不得终年温饱,仅享受水准极低之生活,大多数为赤贫……与美相比相差十八倍收入。”美国学者估计,1930年代中国农民的死亡率大约是世界上最高的,高于美国死亡率2.5倍,甚至显著高于印度的死亡率。众多关于中国农村调查报告的立场、视角和背景虽然不同(如政府调查、国外机构调查、民间社会调查与学界调查等),但由此呈现的基本数据和概况也还是可供参证的重要资料,可以从其整理的数据和史实梳理中获得一个相对共识或基础性判断。
朱羲农在《十年来的中国农业》写道:“自从民国纪元以来,因为内乱战争及举行新政之故,关于农民的赋税比较从前超过得很远……因此,农民中便发生一种极反动的感叹说: 倒是专制时代好,民国所给予我们的苦痛太大了! ”时人指出,正是在“黄金十年”时期,“中国农业,近十年来,无疑的已经发生了极端严重的危机”。20世纪30年代,中国乡村危机的时代特征十分显然。对此,《东方杂志》的一位记者写道:“农业的中国已开始入于工商业化的时代,于是农民的困苦比从前更甚。”(《农民问题与中国之将来》)这是超越经济领域的一种全面危机,是一种“农村总崩溃”。它是由政治纷乱、经济破产、社会失序、文化失范所引发的整体危机。而且,这是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进程而出现的乡村社会急剧衰退的危机。1930年周谷城在文章中指出:“结果都市日愈繁荣,农村日益衰落。”“从都市到农村切断了农工商相互间的纽带”,“大都市作了病态的繁荣”,“农村相继破产”(《中国社会之变化》)。某种意义上说,乡村危机也是传统时代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破解后的必然结果,它是工业化和城市化非均衡发展和繁荣的另一极的负效应。在“都市的发展,其反面就是农村的崩溃。使农村加速崩溃的种种事实,同时就是使都市发展的事实。”总而言之,“中国近几十年都市发展的事实,恰恰是破坏农村的。农村加速度的崩溃,便促成了都市的发展……过去几十年的事实却是如此的”(《中国社会之变化》)。
揆诸史实不难判断,乡村危机实际上并不是乡村本身的危机,而是近代城乡背离化发展态势下所造成的乡村社会、经济、文化全面衰退危机。傅葆琛在《乡建运动总检讨》中指出:“城乡两区,一个迈进,一个落后,形成一种畸形的现象”(《傅葆琛教育论著选》)。而在南京政府十年间,由于“农产品的价格日形低落,而日用品的价格飞速上涨……农民的生活愈加艰难。”(朱羲农)虽然国民政府也推出了农业改良的措施,却影响轻微,正如何廉所说:“从1927到1937年这一时期,在农业发展上,就全国而言没有超出过计划阶段。”因此,仅仅聚焦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增长的“黄金十年”的认识,恐怕既不足以呈现民国前期历史发展的整体面相,也无法揭示其历史发展进程的实相。

“黄金十年”呈现出自身的危机
其实,即使从现代工业增长本身而言,其发展的速度与质性也极为有限,能否以辉煌的“金色”加以定评?其实,时人在横向与纵向的比较中已有过较为客观的评估。
据1933年中国统计研究所调查统计,17省之工业(东三省除外),全国工厂不过三千家左右(包括未调查者在内),工人总数为214736人,动力总数马力为226085.45匹。平均每十五万人仅有工厂一家(洪丈里:《民元来我国之工业》)。国民政府“欲急起直追,然在短短数十年的时间中,于战乱相继,民不聊生的情形之下,亦断难迎头赶上。在人家是以工业为后盾,商业为前锋,在我国则既有前锋,惜无后盾。”(骆清华:《民元来我国之工商业》)因此,民元以还,中国工商业由传统保守之道路,走上与外货竞争本国市场的阶段。不过,从进出口贸易情况可知,此“黄金十年”间的历史与既往并无明显改观,“只有以传统之土产,谋抵巨量之入超,此一招架方法,数十年来如一日。”打开八十年来之海关进出口统计数字,几乎年年入超,“我国工商业之危机,迄今没有一日或离。”此间,现代工业虽亦持续增长,“然其范围狭小更未步上重工业之途,仅有轻工业中之几项主要者,稍具眉目而已。然亦无可讳言……国内基本工业基础尚难奠定,亦不能达到自给自足的水准。”甚至,“民国奠定以来,我国之潜在财富,连年不断的在向外流出”。
纵向比较中亦可发现,就现代工商业的发展而言,比较乐观之阶段“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时期。”此间,民国纺织工业“即飞黄腾达……其总数约增加百分之五十左右。多数工商业皆能获得盈利,除此以外,则无时不在不景气空气笼罩之中。”(骆清华:《民元来我国之工商业》)实际上,在1936年前,“中国工业生产通常以一个不变的速度增长,这一事实也让人认为南京政权的政策不可能显著地促成工业的增长。它表明,基本的社会和经济力量正在朝着工业发展的方向起作用,而与政权或政府的政策无关。”
所以,总体上看,在所谓民国“黄金十年”期间,“一则新式工业根本未走上现代化之途,再则受帝国主义之政治的、经济的乃至军事的严重压迫,进步究属有限”(骆清华:《民元来我国之工商业》)。实际上,当时的中国工业品除丝织品、植物油尚可输出,火柴、卷烟、针织品尚可自给外,其余大部分都不可以自给。现代工业在发展中也呈现出自身的危机。
(作者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标题为编者所拟)
(原标题:民国“黄金十年”的真实面相:农村陷入“总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