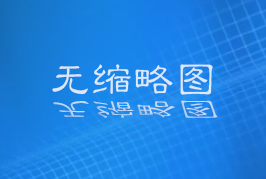被驯化了的摄影
罗兰·巴特著,赵克非译
选自《明室:摄影纵横谈》,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
社会在努力使摄影变得规矩,竭力抑制摄影的疯狂,那种疯狂时刻都有在看照片的人脸上爆发的危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社会有两种可用的手段。
第一种,把摄影变成艺术,因为任何一种艺术都不是疯狂的。这样一来,摄影师就可以一味地和艺术家去竞争,让自己专心致力于画面的修饰,致力于曝光方式的考究。
摄影也许真地能成为艺术:照片上再没有了丝毫的疯狂,摄影的真谛被遗忘了,其实质因而不再对我起作用了。面对普约的《散步的女人》,你以为我会被撩拨到大叫:“这个存在过”吗?电影参与了摄影的驯化过程——至少故事片参与了,故事片正是人们所说的第七种艺术;一部影片可以被人为地变得疯狂,可以表现疯狂的文化特征,却永远也不可能在实质上是疯狂的;影片总是幻觉的对立面;它仅仅是一种幻象;影片的幻象是迷惘的,而不是近事遗忘的。
另一种使摄影变规矩的手段,是普及摄影,使摄影“合群”,把摄影变得平凡,直至使摄影和任何图象相比再无突出之处,不能再显示它的特点,它的愤世嫉俗,它的疯狂。
在我们这个社会里,目前的情形就是这样,摄影已经专横地压倒了所有的图象艺术:雕塑没有了,画像没有了,今后如果还有,也只是慑于(或者说惑于)摄影而当作拍摄模特了。面对着咖啡馆里那些喝咖啡的人,有个人对我说——他说得很对:“您看,这些人多么没有生气啊!现在,照片都比人有活力。”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特点,可能就是这种颠倒:我们按照一种被普及了的想象出来的事物生活。
看看美国吧:在那里,一切都变成了照片:在美国只有照片,只生产和消费照片。举个极端的例子:请您走进纽约的一家色情夜总会,在这家夜总会里,您看不到什么不堪人目的事,只会看到一些栩栩如生的大照片,而照片显示的就是那种不堪入目的事(马普勒托尔普很清醒,他把自己的一些照片从中抽了出来);照片上那个被捆起来抽打的不知名人物(没有一个是演员)要想体会自己的快乐,好像只有将这种快乐和老一套的(过了时的)施虐淫兼受虐淫的图象结合起来时,才有可能:享乐得通过图象:这是个巨大的变化。
这样一种颠倒必然要提出这样一个伦理道德问题:不是说照片是不道德的,反宗教的或属于魔鬼的(就像摄影刚一出现的时候有些人说的那样),而是因为,在被普及之后,摄影打着彰显人类世界的幌子,把这个充满着矛盾和欲望的世界彻底地虚化了。
所谓的先进社会,其特点在于这样的社会今天所消耗的是照片,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是信仰;因此,这样的社会多了些自由,少了些狂热,更自由了,但也更“虚假”(不那么“真实”)了——在时下的意识中,我们把这件事解释为一种招认,对令人厌恶的烦恼情感的招认·,就好像摄影在普及的过程中造成了一个无差别的(冷漠的)世界似的,于是,从这个世界中就只会由这里或那里发出无政府主义的呼声,边际效用说的呼声,个人主义的呼声:让我们把那些照片毁掉,让我们来拯救那个直接的(没有中介的) “欲望”。
疯狂抑或理智?摄影可以是疯狂的,也可以是理智的:如果摄影的写实主义是相对的,被经验或美学的习惯(在理发馆或牙科医生那里翻翻画报)改变得有节制了,它就是理智的,否则,它就是疯狂的:如果它的写实主义是绝对的,而且,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是原始的,是使“时间”这个字在有爱心、受过惊吓的意识中重现的:那是一种纯粹起诱导作用的,可以改变事物进程的情感,是我为了使摄影的“迷人之处”变得更为完美丽呼唤的情感。
摄影就这么两条路。是使摄影的场面服从于完美幻想的文明寓意,还是正视摄影不妥协的真实性的重新活跃,就看我如何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