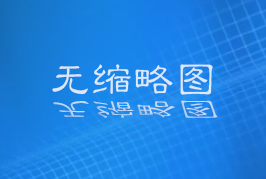每当有人谈起他们的家乡,我就满怀好奇地听着:内蒙古的呼伦贝尔每年九月就迈入了冬季,从窗户向外泼出的水在半道上结了冰,落在地上能发出哗啦一声响;山东淄博的一个小城里,家长里短的事儿总像带着翅膀一样传得飞快,在路上转个身的功夫就能和一打熟人面对面儿;而属于皖南古镇的,照例是长着青苔的光滑青石板道和顺着屋檐淅淅沥沥滴落的雨……
我身边的每个人似乎都成长在那么有意思的地方,他们的记忆都被打上了鲜明的烙印。而我呢,我不无嫉妒地想,一定没有人想听我的故事——毕竟,马鞍山有什么可说的呢?
确切而言,是属于我记忆里的那个马鞍山没什么好说的。它本就不大,而作为我故乡的那部分就要更小,得除去和县、含山、当涂三个县和一个博望区——我压根就没怎么去过,即便是去,也是当作就近的旅游景点。这样一来,真正属于我的马鞍山,不过是由雨山和花山两个区构成的小小一亩三分地,就像中国上百个城市的市区一样,默默地、平凡地生长着。
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马鞍山市里人,在这里出生,也在这里成长,没有遍插水稻的乡下老家,没有波澜起伏辗转迁徙的经历,有的只是我这双年轻的眼睛,和短短十几年间围绕着我和我身边人发生的故事。若从这个角度出发,倒是有些东西可说。或许在这娓娓叙述中,我们都能不经意间嗅到独属这片土地的一缕芳香。
作为一个记事很晚的孩子,四五岁以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在我的脑海里就像是吱吱嘎嘎播放的一部老电影,只有偶尔几个片段色彩鲜明,绝大多数都归于空白和模糊。
我只记得我成天和一帮孩子在小区正中的花园里疯玩,有时候是无意义的追逐打闹,但绝大多是玩“过家家”。我总是担任妈妈的角色,神气活现地指挥众多“儿子”和“女儿”去摘菜(不过是些野花野草)。等他们用手捧着成果回来之后,我就挑一块平整的石头当案板,用树枝将“菜”搅碎模拟做饭,嘴里还要照例说上那么几句:“孩儿他爸就知道干看着,也不来帮帮忙。”即便如此,扮演“爸爸”的那个孩子是绝对不能来帮忙的。他最好明智地选择继续“干看着”,否则就会被剥夺权利,赶到儿子女儿那堆去。至于为什么不能来帮忙,这可能是存在于那个年龄段孩子思维里的固定印象:妈妈就要贤惠,为家务忙碌;爸爸在外工作一天,回到家里来就可以安心休息,什么也不做。但我家恰恰是家务均摊,爸爸做饭,究竟为什么能自然而然和其它孩子达成一致,是我到现在也想不通的地方。


说起来,我奶奶也是个有意思的人。她祖籍在江苏苏州,但自小在上海长大,又作为建国后第一批被分配来开发马鞍山的工程师,代表马钢去往全国各地甚至德国谈生意,在当时那个年代算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奶奶极少跟我聊关于她的事儿,然而逢年过节,串亲访友,大家免不了追忆追忆往昔,我也就在一年又一年里了解地越发深入。据说她家早年是在上海做水果生意的大户,奶奶是正宗的大家小姐,因此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也正是在上学的时候她结识了一个男同学,那个男同学就是后来当了马钢技校老师的我爷爷。
至少在我的印象里,这对夫妻是两个极端。爷爷高高瘦瘦,奶奶矮矮胖胖;爷爷的头发细细软软,贴在头皮上,奶奶的发质粗硬,不打理就四处乱翘;爷爷来自宁波,喜欢吃咸,每餐必有水产,奶奶来自苏州,性嗜甜,无肉不欢;爷爷一没事就外跑,总是带回来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或许是一个盆栽,或许是一块旧手表,或许是一个不知道什么朝代的瓷瓶,他总是忍不住悄悄向我炫耀,然后我就去告诉奶奶,奶奶一听就暴跳如雷,骂他“天天去买别人不要的破烂玩意儿”……这两个人一见面就像是水遇到了火,激得滋滋冒烟,吵起来嗓门一个比一个大,但就是这样打打闹闹地竟然也过了大半辈子。
我曾经很怀疑爷爷奶奶为什么要在一起。“是因为爱吗?”我问他们。就像所有老一辈人对所谓“爱情”闪烁其词一样,他们告诉我,是因为“合适”。合适吗?好像并不合适吧。但也不是因为爱情。那是因为什么呢?当时的我百思不得其解,时间久了也就不再深究,这个问题便渐渐从我的脑海里淡去了。
到了小学四年级,山南小学改换了校址,搬到钢城花园附近,名字也变成了冗长的“马鞍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山南小学”。迁校给我带来最直接的影响,除了作业本封面填起来特别麻烦之外,就是离我家更远了,我便改回位于鹊桥小区的奶奶家,即使如此,走一趟下来也至少要二十分钟。因为奶奶忙着烧饭,没那么多闲工夫一来一回地折腾,就特批我自己上下学。于是那一段呼朋唤友、潇洒自在的日子就开始了:我每次提前四十分钟出发,先到附近的李奶奶家叫上小丽,跟她讲述今日份的故事,一路上又能碰到储储、小敏、小洋……人越聚越多,最后浩浩荡荡地涌进学校边的小卖部,花上几块钱买点零食解解馋。这是上学时的通常情景。但放学后的情况或许就有点不一样了。
实际上,在学校与奶奶家往返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从鹊桥小区和钢城花园内部穿过,其间只需要跨越一条没什么车辆的小马路。因为安全系数相对较高,也便于顺道召结同行伙伴,所以它是广大家长心目中的首选,也是我们日常上学走的路;第二是顺着小区外延的车道走,优势在于长度更短,而且可以经过一个特别吸引我们的地方,那就是朱然墓。

朱然墓是我们本地人的叫法,其正式的名字当为朱然文化公园,是三国时期吴国大将、当阳侯朱然的坟墓所在地,作为迄今为止已发掘东吴墓葬中墓主身份最高、墓葬规模最大、时间最早的一座大墓,而被列入了八十年代中国考古十大发现之一。其中最有名的文物要数那双1700多年前的漆木屐,它的出土甚至引起了世界震动。但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朱然墓的吸引力显然不在于此,也不在于什么仿汉建筑和三国遗风,纯粹是因为它场地够大,够安静,还有墓室和一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可看,算得上是个能撒疯的好地方。
不记得有多少次,我和小伙伴下了课立马狂奔而来,把书包往地上一摔,就开始满园子乱窜。我们在大片的草地上嬉戏奔跑,坐在木质长凳上边聊天边吃点心,低着头仔细看每个花纹不一样的井盖;我们和朱然的雕像打招呼,猜测锻铜浮雕墙上究竟画了点什么,赌输了的人就得溜进黑洞洞的墓室里去……这是专属于我们的时间。再晚一些时候,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来这里散步,还会有许多溜冰玩滑板的小孩和哇哇大哭的婴儿,那就太吵闹也太拥挤了。远自三国时代传来的铮铮古角,似乎也在这浓烈的人间烟火气中被渐渐削弱,乃至于消弥无形。
从四年级到六年级,我花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踏遍了朱然墓的每个角落。但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我很快就迈入了初中,还好巧不巧碰上了全初中最严格的班主任黄老。
没有马鞍山人不知道成功学校。这个原马鞍山二中的初中部,后来的民办初等中学,有着“全市前十名,成功占一半”的美誉。而在成功广大师生群体中间,黄老又是个所向披靡的存在,这个有着近三十年教龄的老教师,用自己丰富的教学经验总结出了一条原则,并矢志不渝地贯彻着,那就是“寒门才能出才子”。
在黄老的理论中,太松散太安逸的孩子会丧失竞争的勇气,只有自始至终严格要求自己的人才能走向成功。拜她所赐,我这初中三年的生活确实和“富贵”毫无关联:我们初一的教室是一间仓库,正对着雏鹰雕像,高高的墙壁上顶上开了几个小窗户通风用;初二的教室是二层最靠里的一间,为了图个清净和与世隔绝;初三更惨,黄老给我们申请到了顶楼露天唯一的一间教室,可谓是冬凉夏暖,八面漏风,四周的防护杆像监狱的铁栅栏一样密密匝匝地立着。关不严的门上有副对联,右边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左边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也不知道是多少年前贴上去的,原本朱红的颜色在风吹雨打下早就褪尽了,反倒把这块地方衬得更加破烂不堪。我们逼不得已,只好收拢心思,专心学习,个个像和尚尼姑一样无欲无求。假如只是物质条件差点我还能忍受,关键黄老还热衷于折磨人的精神:她不但要求我们学好她教的英语,还要语数英政史地理化生九门课样样精通;别的班用来自习的班会课上,我们都得上台演讲和辩论,往往还要忍受辛辣的点评;她绝不允许我们在体育课上到一半的时候溜回来,总是时不时从教室门口路过逮人,美其名曰“身体好才是根本”;有她在,教室必须一尘不染,自己所站的那块地上但凡有一丝灰尘,都要蹲下来擦干净……黄老似乎永远板着脸,瞪着眼,而我们无论多么努力,都是“还不够好”,都是“还可以更好”。她把严师和更年期老太婆的形象维持得那么完美,以至于让我一度相信她就是那样的人。
我到现在还清晰地记得,毕业那天,黄老竟然冲我们笑了。不是微笑,而是开怀地大笑,笑得脸上细细的皱纹都像花一样绽放了,她说:“你们做得很好,每个孩子都有学上,还有那么多能进二中。我一直担心你们有些人初中毕业就走上社会了,那真的太早了,以后会很不容易。我以前对你们严格要求是对你们负责,恨我怨我都没关系,希望苦就苦这几年,至少以后不会后悔。现在你们毕业了,我也就用不着再凶你们啦。”黄老夸奖了我们每个人,包括我成绩倒数的同桌,说她“多才多艺,是个好孩子”,把小姑娘激动得热泪盈眶。
当时我不过觉得黄老的性格也不是那么古板严肃,直到我进了以学风自由而著称的二中,发现我没有像身边的大部分人一样需要经历磨合期,才惊觉黄老用了三年时间培养我们方法与习惯的重要。她是个真正意义上的好老师,虽然有那么些偏执,但能遇见她是我莫大的幸运。我到现在也这么觉得。
以往的日子都可以算得上风平浪静,上高中那会儿,我家却发生了几件大事。首先在高一的时候,我的外公去世了。这是一件谁也意料不到的事儿。自打我有记忆起,外公身体就倍儿棒,基本上从不生病;但没想到这一生就是大病,而这一病,就再也没好。一切的起因不过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多年的老烟枪外公在小辈们的劝阻下,终于下定决心戒烟了。凭着外公超凡的毅力,我们谁也没怀疑他能做到,事实的确如此,但这一戒烟就坏了事。高一上学期快结束的时候,他老人家突然觉得身体乏力,精力衰退,到医院去一检查,没想到竟然是肺癌晚期,医生给出的理由是:肺部环境的突然改变(从有烟变成无烟)导致了癌变。 虽然经过全力治疗和手术,但终究大势已去,半年后,外公便撒手人寰。对此感到最痛苦的,自然是失去老伴的外婆。
外公外婆与爷爷奶奶不同,他们是土生土长的马鞍山人。外婆家里兄弟姐妹众多,家境贫寒,供不起所有孩子上学。作为女孩,外婆只念到小学六年级就辍学了,其后一直在纺织厂做工补贴家用,成年后便嫁给了当小学老师的外公。在当时那个年代,穷教师和纺织女工的收入自然是微薄的,但即便物质上有所匮乏,在我妈的描述里,这对夫妻十年如一日的恩爱,一辈子都没红过脸。在没什么文化,大字不识几个的外婆心里,外公什么都会,也什么都懂,他是家里的顶梁柱,是最明智的参谋,也是她最坚实的依靠。外公一走,外婆的天就塌了。
在外公的葬礼上,我们穿着黑衣,披麻戴孝。外婆被人搀扶着,哭得声嘶力竭,直不起腰,反反复复叨念着:“老芮(外公)心肠那么好,老天怎么忍心这么早收他?”大家都附和着,低声呜咽着,我却出奇得没有多么悲痛,只感到一阵冰冷的空虚。奶奶牵着我的手,远远缀在队伍最后,她沉默的目光越过人群投在被抬起的棺材上。爷爷则一如既往地快步走在前面。我不知道他脸上是什么表情,只能看到他的背影,高高瘦瘦的,在我的印象里从未改变。
有句话说得好:“时间会冲淡一切。”尽然,也不尽然。外婆本来以为离了外公她就活不下去,但事实证明,这世界上谁缺了谁都能过。我上了高三,她也渐渐从悲恸中走了出来,开始代替外公给我们烧饭,开始学着自己思考,自己处理事情。她渐渐哭得少了,抱怨也少了,我妈和小姨都很欣慰,说外婆终于把外公放下了。真是这样吗?每当我路过客厅,总能看到外婆一个人翻着老照片,或是望着窗外发呆。她的真实心情到底是怎样的,谁也不清楚,我只能透过她故作平静的外表隐隐窥见其下的波澜。
外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特别羡慕我爷爷奶奶,说他们这对老夫妻过得又潇洒又年轻。但很快,不幸的阴影也笼罩到了他们身上。就在他们俩准备外出旅游的前个晚上,爷爷突发脑梗,被送去了医院。其后的几天里,病危通知书像雪片一样下。医生都说没救了,差不多准备后事吧,但爷爷却奇迹般地挺过危险期,活了下来。活着,固然令我们欢欣鼓舞,但活着并不代表完整,并不能体现生命的质量。爷爷左半脑的损伤毕竟是不可逆的。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他在往后的日子里不得不承受右半身偏瘫,失去语言功能和智力下降的后果;这就意味着他再也不能和奶奶拌嘴,再也不能站在讲台上侃侃而谈,再也不能偷偷溜出门买回来一大堆“破烂玩意儿”了。
这对老夫妻身边原先总是剑拨弩张的气氛一夕之间松弛了下来,变得前所未有的和谐,也变得前所未有的陌生。奶奶应该是感到很寂寞吧,我想。自从爷爷出事以来,奶奶没在我面前掉下过一滴眼泪,还是像以前一样笑眯眯的。但她老得很快,头发顷刻间全白了,富态的脸庞也爬上了皱纹,跟我说话时总像心不在焉的样子——她一门心思都系在了爷爷身上:操心爷爷的健康问题,奔波着给爷爷找合适的疗养院,给护工塞小礼物希望能更尽心尽力一点……这个她嘴里的“老不死”、“老东西”归根到底还是相濡以沫了大半辈子的老伴,是她“最爱”的,也是“最合适”的人。有时候怯于言语表达,并不代表不在乎。
我不知道外婆和奶奶究竟谁更不幸,但这些倒霉事儿却意外让两个老太太变得亲近了许多。她们之间本来隔着一道文化或是心理的无形屏障:奶奶有着作为知识分子的傲气和大小姐的矜持,而这正是让外婆感到不舒服的地方;外婆感兴趣的家长里短、邻里八卦,又得不到奶奶的共鸣。她们两个的见面一般止于礼貌的问候:“亲家来了!”“哎!亲家好!”然后便各找各的儿女去。但现在,共同的不幸遭遇似乎把这道屏障冲开了一个缺口,她们说起话来也就情真意切了许多:“哎呀!亲家啊,要多多注意身体!”“我身体好着呐!倒是你,照顾那口子挺辛苦的吧!”“没事,不累不累。”听说最近这两个老太太还在私下里互赠慰问品,弄得人哭笑不得。
上了大学之后,我就没有什么机会回家了。隔着一段不远的距离,家乡于我,竟从亲身经历的叙事长诗逐渐剥落成了零碎的话语,经由他口偶然传来:听说我小时候玩耍的花园里重新铺了草皮,添了许多新品种的花。为了美观起见,还把最中间那棵盘根错节的老树换成了一株生机勃勃的树苗,估计得长个十几年才能给孩子爬上去;听说朱然墓换了个气派的大门,红漆刷的柱子,匾额都是用篆文写的,吸引了一大批游客前来参观,从早到晚都闹哄哄的;听说成功学校被另一所中学收购,翻修一新不假,但逼走了一大批老教师,也不知道黄老还在不在……我不过离开了短短两年,童年的想往和少年的记忆便无所归依。那些久别回乡的游子,眼前所见,怕不是沧海桑田?
我对家乡到底还是眷念的,即便它看上去平淡无奇。在这片土地上,有爷爷奶奶,有黄老,也有外公外婆和林林总总的人,大家江淮方言交杂着吴语,马普应和着土话,混杂又和谐地过着日子。
马鞍山只是个小城市,它安定不了年轻人逐梦的心,却将挂念牢牢地系在每一个离去的孩子身上——这儿依山傍水,有着江南的婉约,有着舒适安逸的慢节奏生活,还有着无法割舍的回忆。只要回忆还在,没有人能真正离开。
听奶奶说家乡的秋菊开得正旺,我也是时候回家看看了。
(返乡导师汪成法,安徽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作者简介】
我是范榕,安徽大学16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安徽省,马鞍山人。
我原本以为所有的城市都大同小异,马鞍山不过是其中最平平无奇的一个。但等我真正离开了家乡,离开了养育自己一方水土后才发现,其实每个城市都震荡着属于自己的鼓点。四散的游子们正因为踏着故乡的节奏,所以无论走到哪里,都维系回忆与牵挂。
图文 | 范榕 出品|头号地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