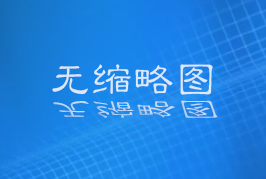中国人喜欢足球吗?在很多人看来,这几乎没有疑问:看每四年一届的世界杯就知道了。无法否认的事实是,没有任何一项体育竞技类比赛,能够如此吸引全民级别的关注,尤其还是在中国国家队常年缺席的状况下。
世界杯对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来说,就是场四年一度的狂欢。它就好像一场打破分化和规则的狂欢节,是一种对社会原有状态和既定体系的逃离,人们以更加崇高的,节日性的目的,换取短暂的与现代社会的和解。人回归某种原始性:工作状态和休息状态被更加鲜明地分隔开了,在世界杯进行的过程中,休息等于观看比赛,观看比赛即等于娱乐。
而这种娱乐被赋予了等于敬神的新价值。足球比赛的结果、技战术都永远只是附带,人们作为球队支持者的情绪和归属感,超越运动本身成为一种符号。中国代表队的缺席正是对狂欢节的好辅助;民族主义在这一刻退潮,个体以无数任意性的理由进行选择和分野,产生无数的团体进行相互平等的对话。
那么,对世界杯的狂热,就意味着中国人喜爱足球,就能搞好足球吗?

世界杯,狂欢节与现代足球
上文所述的这种狂欢性,是俄国文学理论家米哈伊尔·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的后半部分着重讨论的话题。他以拉伯雷小说中体现出的中世纪狂欢节习俗为例,讨论了在这种狂欢的状态下,人对一切社会固有习俗的暂时打破所产生的,某种依靠节日来形成的乌托邦。此时,节日的主题(足球)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节日所赋予的本体论式的,自给自足无法质疑的狂欢性。等到世界杯尘埃落定,冠军决出,除了夺冠球队的拥趸还要庆祝一段时间之外,其他所有参与这场狂欢节的人,都恍若梦醒,迅速从狂欢节上抽离,回到日常的生活规训中。
同样的,回到足球比赛上来说,比赛的过程并不重要,比赛的结果才是狂欢节唯一需要的对象:技战术层面的精彩只能引发足球爱好者的愉悦,而结果的理想,才能够引爆巴赫金所谓“普罗万象”的狂欢。有关比赛结果的狂喜、悲伤、愤怒、辱骂、甚至赌球的行为,我们可以指责,可以愤怒,但同时也会理解这是一种谵妄:谵妄的来源,正是狂欢节的施魅功能。狂欢节中,理性和现代性都成为敌人,潜意识和心灵的权力取得的短暂胜利,得以耀武扬威:在节日的逻辑之下,这都是可以允许的。
这是中国人普遍的一种对世界杯、对足球运动的理解。也因此,中国足球国家队的成绩成为了大众关注的,甚至是唯一关注的焦点。2019年开年中国队征战亚洲杯,这是中国队目前所能参与的最高级别的洲际赛事。中国队最终打入八强,满足了赛前最基本的成绩目标;而从球迷关注的角度,“赢球就是硬道理”的观点,也成为广泛主流。体操奥运冠军陈一冰有关“赢个泰国队为什么要这样大肆庆祝”的言论,集中受到球迷反对,被认为是 “不懂球”——中国人对于足球赛事的节日和狂欢节逻辑,在这里也得到体现。我们可以以18年前中国队唯一一次打入世界杯的经历作为基础来畅想,一旦中国队再次进入世界杯舞台,甚至取得了突破性的成绩,世界杯所带来的狂欢效应,又将在中国呈现多少几何倍数的增长。
这里产生的疑问是:足球赛事真的等于狂欢节吗?足球运动的内在逻辑真的就是狂欢节的逻辑吗?
追溯现代足球的历史,我们可以说,早年的“足球”,中世纪的足球比赛,完全符合巴赫金所描述的狂欢节特征。12世纪的英国,足球比赛成为城镇之间固定一年两次的集体狂欢项目。当时的规则是这样的:比赛当天,两座城市停止所有的生产活动,具备能力的市民全部参与进来。在两座城市的边界,裁判开球,双方一拥而上,手脚并用,目的都是将球送到对方城市的市中心规定的区域。在这个全民参与的过程中,两座城市任何一块土地都是赛场,为了争夺球权,进入居民住房,砸坏屋内陈设也是常有的事,不参加比赛的居民往往紧闭门窗,生怕球和参赛者进到屋子里来,因为在比赛中造成的损失是无人赔偿的。比赛没有时间限制,往往要持续一天,直到一方将球送到对方市中心为止。《哈利·波特》系列的魁地奇运动中“不抢到金色飞贼比赛就不结束”的规则,也可能与这一中世纪狂欢规则密切相关。
然而这样的大规模的狂欢,必然不再符合时代发展和城市生活的需要,单场比赛的赛场大小、参与人数和比赛时间开始被缩减,项目规则也逐渐规范起来。1848年《剑桥规则》的产生,标志着现代意义上11人制足球运动的诞生。
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提出,新教伦理对“天职”和“责任”的理解,使得“理性化”成为达到目标的手段,促使市民生活中各行各业的分化和规范化,最终形成运转良好的社会系统。而足球规则的成文,其实也标志着足球从狂欢节,从节日庆典被转化为一门专业的体育竞技项目,它在被限制了比赛时长、参赛人数、场地大小、持球方式等等的同时,也被日常化为一种随时可以进行的赛事,并逐渐成为当地人民的文化生活内容。1863年,英格兰足总杯开始举办,1888年,英格兰足球联赛开始举行,一百年多持续不断的赛事,培养了英国深厚的足球文化并影响到了全世界。
事实是,当英国几乎每个社区都有代表社区的球队参加联赛和足总杯时,当英国的球迷每周都要到球队主场观看球队的比赛时,当一家人祖孙数代都是当地球队的支持者甚至在球队主场享有专属座位时,足球本身意义上狂欢节的一面已经消褪,足球作为最古老的、最传统的一项体育竞技,已经成为了一种商业行为和生活方式,日常化、规范化和商品消费逻辑让这个源自狂欢节的项目彻底被资本主义系统所规训,也让对足球的爱好彻底融入了市民生活的肌理和血液之中。
现代足球,是伴随日常生活而自行生长的一种共生主体,早已不再是打破规则,普罗万象的客体狂欢节了。
搞好足球的标准是什么?
现代足球的去狂欢节化,首先表现在赛事的频繁和日常性上。对于一名球员来说,从他开始在俱乐部踢上比赛开始,他未来十到二十年的职业生涯就几乎被填充完满:首先,他要参加每年俱乐部的联赛,包括国内联赛和洲际联赛,这意味着一年中9-10个月的时间每周都有比赛参加;而在没有俱乐部比赛的时间段,又有国家队比赛,世界杯、洲际国家杯、奥运会等比赛都在联赛间歇中进行。而对于球迷来说,这也意味着每周都有相当数量的足球比赛可供观赏,“狂欢节”所需要的稀缺性和节日性,已经逐渐沦落为对某些特殊赛事的期待(如欧冠决赛,世界杯,欧洲杯,联赛关键场次等),失色不少。
其次,是发展成熟的商业体制,使得足球赛事不再是普罗大众都能轻易参与的狂欢项目,而成为技术高精尖的对决。人们常说足球变了,不再是一门运动,它是战争;甚至它已经不再是普通的冷兵器战争,不再是对垒的阵地战,而成为某种工业化的,流水线式的未来虚拟战争。训练项目和赛前、赛后准备的大数据化,比赛速度被不断加快,球场空间被切割压缩,攻防逐渐一体,技战术思想越发极端(如传控战术的极端是使对方无法控球、防守反击的极端是使对方放弃防守),对参赛运动员个体的需求走向功能化。类似“古典前腰”、“有球踢法”、类似1982年那支“艺术桑巴”风格的巴西队,都像手工业者一样带着灵光余韵在尊敬和惋惜中不可避免的消亡了,对它的仁慈和悲叹,无非是为了掩盖不可挽回的绝望。甚至在悲观的人看来,现代职业足球可以转化为十一个AI仿生足球机器人之间的对抗,比赛可以最终演化为沙盘推演,推向这项运动规则限定之内所能达到的肉体、精神和交互的极限。
其三,从整体性上对比赛成绩重要程度的取消。固然各支球队比赛的目标是夺得冠军,但冠军终归是少数,常年没有冠军是大多数球队的常态。随着商业资本在各支球队占据力量的多寡,现代商业足球在俱乐部范畴内同样形成了某种分工:专注夺冠的明星球队,重在青训的热血青年军,依靠买卖球员牟利的培养工厂……缺乏胜利带来的狂欢式愉悦,并不意味着快乐的丧失,球迷们根据俱乐部的实力和定位产生了各自不同的期待,各支球队都能稳定地在自己的舒适圈内有条不紊地运转多年。而这种期待的分化,一方面保证了每支球队都能得到相应关注,却也破坏了狂欢节所能带来的参与者极致的地位平等和对话性。比赛结果不再是掌上的明珠,狂欢节也失去了庆典所需要的祭品。
然而,现代足球这些鲜明的去狂欢化特征,在中国显然是并不适用的。对大多数国人来说,家乡并没有足球俱乐部,也并不关注本国联赛,对足球的关注一般局限于国家队参与世界杯预选赛、亚洲杯,甚至相当一部分“球迷”只是每四年观赏一次世界杯,这些群体对足球的感受,是彻底“狂欢化”的;而中国足球虽然已经是国内商业化、职业化体育的领头羊,创造了一定程度的商业价值,但在技战术、赛事准备、球迷素养上却还是非常落后的;也因此,国人对足球比赛最为关注的也毫无疑问是成绩,更具体说,是中国国家队的成绩。
多年来,无论是中国足球的从业者,还是热爱中国足球的球迷,还是最广泛意义上的普罗大众,我们都始终在一个本质上的问题上打转,即:搞好足球的标准是什么?这个问题似乎看起来非常荒谬,因为似乎无论各方如何就搞好中国足球的方式争议不休,所有人的方向都是指向国家队的成绩进步,这似乎是一个不需要讨论的话题:不管是集训、军训、归化球员、豪赌世界杯的“专业体制手段”,还是发展商业俱乐部、发展联赛的“商业职业手段”,或者是纳入高考、U23政策、建立足球学校和青训体系来培养足球兴趣、增加从业人口,无论是什么样的举措,在国内的讨论话语体系里,这些手段的目标都指向唯一的理想化存在:即国足打进世界杯,甚至杀入淘汰赛,甚至取得冠军。而在去狂欢化的现代职业足球文化中,国家队的成绩绝非参与者唯一的诉求,甚至在某些极端状况下,是相悖的。
那么,就算未来国足真的成为世界杯的常客,就算中国的足球从业人口翻上几倍,就算足球再次成为中国当之无愧的第一运动,有一个文化上的、心理上的事实我们总无法忽略: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里,国人对足球的概念和理解依然会是“狂欢节”化的,真正意义上促使职业足球生根发芽的足球文化土壤,在中国必然还是缺乏的;甚至,是不被认为有必要的。当我们回顾自国足从2002年韩日世界杯铩羽而归后,中国足球近二十余年的沉浮史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大家耳熟能详的对中国足球“急功近利”的评价,最终还是要归结于国人长期对足球“狂欢节”式的理解,和对于西方现代足球文化的水土不服。
“过把瘾就死”:我们选择狂欢?
1993年,时任中国足球协会专职副主席兼秘书长的王俊生推出了《中国足球十年发展规划》,标志着中国足球开始了轰轰烈烈的职业化改革,各大省市的体校专业队纷纷接受企业注资和改编,成立商业足球俱乐部参与职业“甲A联赛”,一时间在全国掀起足球狂热。但谁都知道,这一改革固然是追随当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潮流,但从推动动机上,还是源自于国足80年代以来多次冲击世界杯的失败,使中国足球决心放弃举国体制专业体校道路,而从欧美的职业足球文化汲取经验,通过举办联赛来寻求成绩的提升。
举办联赛从而提升国足成绩的逻辑是这样的:商业资金和市场开发为足球带来足够多的关注度,增强社会影响,吸引更多年轻人参与到足球运动中来;与此同时,在联赛的建设中学习欧美先进的技战术经验和球队管理方法,从而提高国足的选材面和技战术能力,最终取得成绩上的突破。这一逻辑在国外显然是经受住百年考验的,被证明是提高国家队成绩的有效方法;但被无情忽略的是,在去狂欢节化的现代足球文化中,提升国家队成绩只是举办联赛这一举措所要达到的其中一项目标之一,绝非唯一的、甚至绝非最重要的目标。这就意味着,通过联赛来提升国家队水平,虽然从长远看来必然能够取得成效,但在十年,二十年这类较为短暂的时间内,具备相当大程度的不确定性。
广大球迷群体和从业人员在面对2019年亚洲杯八强这一并不糟糕的成绩所产生的悲观态度,依然是对建设联赛这一手段对国家队成绩的提升并不立竿见影所致。无论如何强调国足成绩的回暖,未能打进2018年世界杯依然是事实。面对3年后的2022年世界杯,似乎又一场“豪赌世界杯”即将上演。陈一冰在微博上提出的疑问具有代表性,他说,“既然商业化,职业化没搞好,为什么我们不重新用举国专业体制尝试一下呢?”
站在中国足球发展的又一个十字路口,我们似乎应该再次提出这个被认为答案很简单的问题:搞好足球的标准是什么?如果仅仅就是国家队成绩的提升,那么似乎事实证明,借鉴现代职业足球文化的联赛道路,耗时长,不确定性强,并且是一个迂回而不直接的手段;而如果我们再一次回到专业化体制下,也许未来会再次出现2004-2013年的十年寒冬,但却大概率能换来又一次如同2002年世界杯的全民狂欢?
狂欢节的根本逻辑,难道不就是“过把瘾就死”吗?只要我们依然遵循对足球古老的狂欢节逻辑,将其仅仅作为一种带来愉悦的对象客体,那么联赛建设、现代职业足球文化能带来的除国家队成绩的提升之外的其他影响(比如足球人口的增加,足球文化的传播,足球商业价值的增值,足球运动在国人对体育锻炼的选择中更好的优先级——根本上是西方现代足球文化发展的本体性的自我增殖需求)对我们来说,似乎也没有对欧美人那么重要,也似乎不是一定要达成的必然目标?
网络体育论坛“虎扑”上有人这么说:“足球搞不好就搞不好吧,终究也不是什么大事。”虽是绝望无奈之语,但在中国足球当前的环境下,这句话完全成立。相比于要求中国用上百年的时间去复制、培养西方根植于欧洲历史文化逻辑的现代足球文化,似乎还是将足球当作一项没有那么特殊的体育竞技运动,用间歇性的好成绩为国人带来狂欢节式的快感更加“实际”一些?而如果各种“中国特色”的举措真的能够让中国队打入几届世界杯,为国人每四年一度的世界杯狂欢节增添一抹亮色,除此之外,其实也别无所求。
也许我们至今还在方向上迷茫徘徊,更谈何前进;也许我们最终会选择出一条真正适合中国足球的发展道路,究竟我们还要不要用“狂欢节”的逻辑来对待中国足球,还需要足球从业人员用热爱和责任去尝试,去思考;但至少现在,无论每一次有关足球的狂欢节结束之后的我们还会不会在这四年的间隙里继续关注足球,我们都会寻找其他的事物来填补空白。
狂欢节可以是足球,狂欢节也可以有关任何事情:当代的狂欢节永不止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