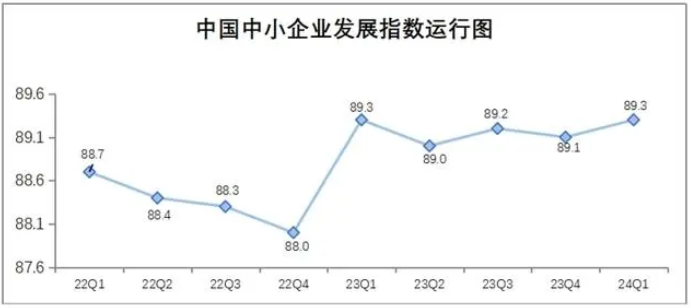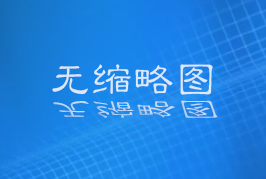有人揶揄,《锡尔斯·玛利亚》(右图)就是一老一少的两个女人在阿尔卑斯山的度假屋里聊聊电影和表演。话是没错,可是当她们在对谈里面对或回避着青春、衰老、感情、欲望和时间这些生命中不能幸免的难题时,女人摆脱被看的客体、发出主体的声音,这样的电影实在是太少太难得。 本版图片皆资料照片


拍出过《土地与自由》、《风吹麦浪》里的批判者肯·洛奇,这个一辈子不妥协的影坛斗士老了,《吉米的舞厅》是他坦诚地流露着暮年的哀伤,命运扼腕的遗憾替代了风刀霜剑的残酷。


本报记者 柳青
每一年,和奥斯卡沾边的电影总是最抢手,《鸟人》《少年时代》《消失的爱人》《爆裂鼓手》《万物理论》《第四公民》《依然爱丽丝》《模仿游戏》《狐狸猎手》……这些电影从去年秋天起在世界各地滚动轰炸,在放开的电影市场,这类电影本来就是院线里的常规产品。可对于此间的观众而言,它们还是“熟悉的陌生人”,听说了很多次,要在影院里看到,只有在电影节展映的场合。
每年初夏时节,在十来天的时间里,我们能在电影院里看到几百部滚烫的新片,有持续制造话题的争议作品,有海外影展上的大师新作,有被低估的新经典,也有更多等待被发现的安静的新片。只盯着一小撮已经家喻户晓的奥斯卡嫡系未免顾此失彼,我们不妨把眼光投向不那么热门的选择,和最新的好电影来一场美好的邂逅。
平静的“小”电影
《邮差的白夜》,开到红莓花事了
“田野小河边,红莓花儿开。”会唱这首《红莓花儿开》的年轻人已经很少,它快要成为上一代人的记忆,而这首歌里唱到的俄罗斯乡野风土,也是一道正在消亡的风景线。一位俄罗斯历史学家曾说,欧洲是石头建的,俄罗斯是木头建的。意思是当西欧在近代疯狂陷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时,俄罗斯延续着以乡村为基础的农业社会,农村是俄罗斯土地的灵魂,俄罗斯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存在于乡村中。但是上世纪末的剧变后,俄罗斯的乡村随着旧的体制一同消亡,尤其在过去的5年里,俄罗斯乡村锐减近4成,乡村文化的命脉在剧变中被抛弃在荒凉的外省。在《邮差的白夜》里,导演冈察洛夫斯基焦虑的正是这种不可逆的消亡,向红莓花开败的乡野投去哀伤的凝视。
冈察洛夫斯基的弟弟是声名显赫的俄罗斯“国师”级导演米哈尔科夫,比起弟弟的大鸣大放,冈察洛夫斯基是内敛的,再强烈的情感也会克制地轻描淡写。他钟爱契诃夫,执着于日常的细微,他喜欢中国古诗,对时间、空间和行动于其间的人的刻画,流露着天地悠悠的怆然之感。在《邮差的白夜》里,他用白描写意的手法去描绘被飞快的工业进程抛弃的村庄、留在土地上的老人们过时的生活,以及邮差落伍的工作方式,这并不是局限于怀旧的抒情,风起萍末,见微知著,这些看似平静的影像未尝不是对抗消亡的一种努力。
《姆明:漫游蓝湾》,让我们把尾巴缠到一起
去年是儿童文学作家和画家托芙·杨松诞辰100周年,为了纪念她,芬兰给她画的“矮子精”姆明拍了一部大电影《姆明:漫游蓝湾》。今年,小姆明70岁,来看这部《漫游蓝湾》还是很应景。
托芙·杨松在1945年写出第一个“姆明谷”的故事,也是她亲自把姆明的故事画成连环画,在25年的时间里她慢工出细活地创作了8本姆明谷系列童话。这群生活在北欧森林里的精灵生物“姆明”清晰地带着杨松本人的家庭生活痕迹。她的雕塑家爸爸渴望冒险,他离群索居的孤独诗意和对大海的热爱,深刻地影响了女儿,在《姆明爸爸的海上历险》的扉页,杨松写下:“献给一切做爸爸的。”杨松一家住在赫尔辛基,每年五到九月,全家会到距离赫尔辛基50公里的泊雾岛上度过北欧阳光灿烂的明亮夏天,如同桃源乡的离岸小岛正是“姆明谷”的原型。杨松笔下的姆明一家,个个自由散漫,做事不按常理出牌,可是他们彼此之间毫无保留地相爱,他们会冒险,会迷路,会做很多不靠谱的事,但牢固存在于家族成员之间的宽容和爱总能让迷失的人找到回家的路。其实,杨松画的是自己的家人呀,1970年,她的母亲去世,她写下《十一月的姆明谷》,故事的结尾,姆明一家在冬天来临前神秘离开,姆明谷的故事在萧瑟的离愁里戛然落幕。
所以,当我们看《漫游蓝湾》时,任何电影的评价原则在这样的电影前是无效的。白白胖胖的姆明们迎着蔚蓝海岸的阳光回来了--温柔的姆明,甜蜜的斯诺克小妞,充满爱心的妈妈和做白日梦爸爸,游吟诗人小嗅嗅和彪悍酷拽的小美,他们都回来了,能再次看到姆明们兴高采烈地把尾巴交缠在一起,就已经很好了。
《四十五周年》,爱是天长地久的误会
结婚45周年纪念,在西方被称为“蓝宝石婚”,是个有分量的纪念日。
一对老夫妻结婚45周年纪念日在即,她忙着筹备派对,一如既往地照顾他,日子风平浪静,突然他们收到一封信,通知男人,他的死于登山意外的初恋情人的尸体,在阿尔卑斯山的冰川里被发现了。然后,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
安德鲁·海格是个很文气的导演,他把《四十五周年》拍得格外冷静,那么大的意外在生活里砸出一个窟窿,可老头不响,老太不怒,大家都藏着。面上波澜不惊,而内心惊涛骇浪,电影的气质就像片子里湿冷的早春,阴飕飕的,但冻土下面淌着岩浆,隐忍着一股没有机会爆发的怒气。导演本人是同性恋,之前执导的片子都是同性题材,这是他第一次处理男女问题。事实证明,婚姻和感情的修罗场上,爱情也罢,婚姻也罢,很多时候只是时机问题,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天长地久的误会。
片子里的男女主角包圆了今年柏林影展的影帝影后,表演的微妙和剧本的微妙层次是极好的呼应。男人木讷,躲避,他的“无为”是这段关系里最冷酷的暧昧:爱或不爱都是模棱两可。在女人这边,生活的厮磨没能钝化感情的锐角,被爱情和婚姻里强烈的排他感和嫉妒所折磨,岁月并不能让她对这些免疫。《四十五周年》里,冲突始终没有机会爆发,但看到最后,触目惊心,就像看到画卷尽头藏着的匕首。
新经典
《吉米的舞厅》,未老莫还乡
老导演肯·洛奇拍摄《吉米的舞厅》的过程中,传出两个消息。其一是由于胶卷公司破产,他用惯的胶片断货了,遍寻不得,后来总算靠着昆汀·塔伦蒂诺几个后生导演各处奔走,把能找到的存货都送到他手上,35毫米胶片退出电影舞台大势不可挡。其二是他说自己年纪大了,精力不济,拍摄资源也越来越不易得,这会是他最后一部剧情长片,他暂时不退休,但往后只给电视台拍些纪录片和迷你剧。
两个消息都是“伤离别”的意思,也就不奇怪《吉米的舞厅》里弥漫着惜别的离愁。有评论认为这部电影“美则美矣,欠缺锋芒”,命运扼腕的遗憾替代了风刀霜剑的残酷,持这样观点的人们怀念《土地与自由》、《风吹麦浪》里的批判者肯·洛奇。可是,这个一辈子不妥协的影坛斗士也老了呀,《吉米的舞厅》是他坦诚地流露着暮年的哀伤。若干年前,安哲罗普洛斯在一次演讲中几乎含泪说出,他们最终都是梦碎的人。
肯·洛奇也是这样,所以他会去讲爱尔兰人吉米短暂的返乡经历,吉米原名詹姆斯·格拉尔顿,1920年代他投入轰轰烈烈的独立运动,在派系林立的局面到来前远走美国。1932年,爱尔兰内战结束10年,在纽约流亡10年的吉米还乡,他的本意是回到故乡平静生活,重新开张一处荒废的舞厅,让那个小角落成为自由思潮的伊甸园。吉米的社会热情从未冷却,理想主义激荡在他的舞厅里,伙伴们跳着踢踏舞,朗诵叶芝的诗,也探讨乡村和工人的出路。只短短数月,这间乡间舞厅已被保守分子烧毁,吉米被捕,当局没审判就用一张去纽约的单程船票把他驱逐出境--他像弃儿一样离开,痛彻心扉地认识到曾经热衷的舞台上没有他的理想容身之地。
整部电影里,导演没有设置剧烈的戏剧冲突,但却点出时代语境的惊人重复:1929年大萧条后被重创的爱尔兰和当下爱尔兰挣扎的困境,有什么分别呢?吉米这个理想主义者的末路,不过是应和了那句,未老莫还乡,还乡需断肠。
《锡尔斯·玛利亚》,她孤独地徘徊在时间之外
导演阿萨亚斯说,有次他和朱丽叶·比诺什通电话,她对他说:“我们拍个电影吧,这么多年了,我没在你的电影里做过真正的主角呢。”本来是句朋友之间半开玩笑的话,结果阿萨亚斯真的开始给比诺什写个剧本,断断续续写了大半年,最后拍出这部《锡尔斯·玛利亚》。
散文化的文艺小品是阿萨亚斯一贯擅长的,但是拍到《锡尔斯·玛利亚》,多年来徘徊在“二甲一等”这个位置的他,开始显露出大师相。这电影看上去轻巧,琐碎,散漫,完全没有成为杰作的企图,甚至有人揶揄,不就是一老一少的两个女人在阿尔卑斯山的度假屋里聊聊电影和表演。话是没错,可是当她们在对谈里面对或回避着青春、衰老、感情、欲望和时间这些生命中不能幸免的难题时,女性以主体的形象在银幕上逐渐清晰。能反出男性视角的垄断,能让女人摆脱被看的客体并且发出主体的声音,这样的电影实在是太少太难得。
阿萨亚斯在一次访谈里提到,他落笔写《锡尔斯·玛利亚》时,心里没有故事的轮廓,他想的只有比诺什,“我不是和她合作一部电影,我要拍一部关于她的电影。”在这里,虚构和真实的边界并不重要,电影里的玛利亚和瓦伦汀是不是现实中两位演员--比诺什和克里斯汀·斯图尔特的延伸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女人怎样面对青春,怎样在泛娱乐化的环境里安放她的才华和追求,以及更严酷的,随着时间流逝,她怎样面对不能阻挡的衰老。就像在片子里的戏中戏《马洛亚之蛇》里,年轻骄傲的希格里德抛弃了海伦娜,她没有意识到海伦娜也曾有过像她一样无畏的过去,她也没有预见到哀求她怜悯的海伦娜将是未来的自己。所谓“马洛亚之蛇”,那是阿尔卑斯山口的奇观,翻滚的云层隐喻着激情和欲望,也是一往无前的时间之流。
在这个意义上,片子里最伤感的片刻,是一个新锐导演请玛利亚在超级英雄片里出演一个角色,他说,“她是超然于时间之外的。”那个瞬间,玛利亚释然了,她决定和自己和解。她回到舞台上,聚光灯下,是一个女人和时间握手言和后的平静肖像。借用王小波的一句话作结语:似水流年才是一个人的一切,其余的全是片刻的欢娱和不幸。
不走寻常路
《味园universe》,大阪青春风情画
快满40岁的山下敦弘不觉间已经成为一个挺重要的日本导演。他是个很好玩的“不正经”导演,有影评人恭维他拍的电影有贾木许和考里斯马基的风范,他很无辜地回答:“我没有看过他们的电影啊。”再比如,他大言不惭“不爱看小津安二郎”,又特别神经大条地在电影节的场合对影评人说“我很爱看成人电影啊!”这么一个十三点兮兮的导演,在电影里反复拍的也是一群会被定义成“卢瑟(loser)”的没正经的年轻人,甩开起承转合的叙事规范,用仿佛很业余的姿态扫描无所事事的青春,反修辞,冷幽默,发掘日常的荒诞性,在小清新泛滥的日本影坛发出了别样的声音。
山下敦弘是大阪人,《味园universe》全片在大阪拍摄,这电影的姿态明确,是一段植根于大阪的记忆,一幅大阪的青春风情画,散发着截然不同于东京的杂乱气息。片名里的“味园”是大阪的一家酒店,建筑颇具地方特色,酒店地下一层是一间风俗饮食店,1960年代是小乐队和不出名歌手活动的俱乐部,1990年代后期没落,2011年关店,但店面被原样保存。据记载,味园俱乐部鼎盛时期,记录在册的公关有1000多人,当时美国的杂志做过一期“日本最大的club”特为介绍味园。片名里的另一个词universe很明白地传递了这部电影的用意,在字面意义上,片子里所有人物、事件发生交集的场所,是味园酒店里一间设计成太空风格的酒吧,同时,这个单词也是明白的隐喻,每天上演着人生百态的味园,何尝不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宇宙。
《西部慢调》,差一点被预告片骗了
《西部慢调》是今年圣丹斯影展滚烫出炉的评审团大奖得主,如果不是上海电影节展映的契机,我们也实在没可能看到这么簇新的片子。一个多月前,它在北京放映时,一票难求,战况惨烈。爱男主角法斯宾德爱到死去活来的怀春姑娘们,和对西部片抱有不切实际的罗曼蒂克想象的汉子们,两股人群奔涌进电影院,结果,双双发现自己被导演调戏了。
这片子的预告片太“混账”,又工整,又正经,误导我们以为这是一部给老派西部片招魂的“写给逝去传统的情书”。西部片的土壤早就不存在了呀,这个空有躯壳的类型已经和萨满教的巫术没区别,对这一点导演心里当然是门清的,所以他的这部处女作长片《西部慢调》根本是“西部乱来”。开场,有马,有枪,有汉子,说走就走的冒险,大西部碧空寥落,黄沙碧血,笃悠悠地把必要元素一一铺展,之后的剧情神展开。想看西部片的汉子懵了,因为导演处处逆着西部片的规矩来,这是部披着类型片外衣的反类型戏仿片。想看法斯宾德酷帅走天涯的姑娘们也懵了,男神变成一个灰头土脸的流氓,而且大部分时候一群糙汉子在扯什么淡?
结尾,西部流氓法斯宾德特别委琐地截胡了男主角--一个文艺少年--的梦中情人,他们幸福地生活了若干年,他一脸严肃地回忆起这段“生命中特别的经历”。全剧终。这时我们简直能感受到导演躲在摄影机后面满满的恶意:看,文艺青年都没好下场,电影里是这样的!
《荒蛮故事》,不野蛮不成活
《荒蛮故事》的6个平行故事,最短的8分钟,最长的没超过30分钟,都是情节一波三折,讲法干脆利落,没一句废话,统统打砸抢暴力解决。这样一部电影在戛纳电影节的竞赛单元受欢迎完全可以理解,导演把悲剧讲成段子,不带社会批判的道德负担,没宏大叙事的野心,就是一出“拉美人民多奇志”的疯癫闹剧。戛纳的竞赛片一部比一部苦大仇深,看到《荒蛮故事》这种松快敞亮的,能换来半天好心情。
戛纳影展结束后,这片子通过互联网资源在本国文艺青年中制造了好几轮高潮,于是它从一部“乱入的参赛片”演变成一部现象级电影,对它的追捧甚至可能比电影本身更意味深长。拍出《荒蛮故事》的导演绝不悲情,也不深情,确切说他挺无情的,与其说这电影欠缺纵深的思考,不如说它欠缺善意。第一个故事作为引子,紧接着银幕上开始出片头字幕,每个名字的出场搭配着野生动物头像,事实上片名的直译就是“野生动物的故事”。电影自始至终散发的“彪悍民族不需要解释”的匪气,和阿根廷社会的普遍情绪有着直接联系。可以不夸张地说,《荒蛮故事》这样的电影是戾气土壤里养出的野蛮结果,阿根廷人民借机到影院里吐一口浊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