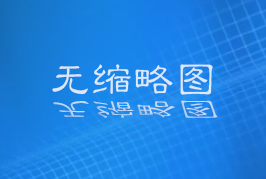当我们今天再来谈论国剧,还可以说些什么?
是“老剧新制”的捉襟见肘,还是“爽文影视化”的视觉快感?如今的国剧面对的质疑声量渐响,但观看国剧的规模却仍在持续壮大。对于国剧不断生成的“越来越美却越来越简单粗暴”的文化认同,既构成了它的现实困境,也直观再现着这一文化产品的群众基础。即便在当前的社会语境中,用“电视机”维系“客厅文化”的传统正在被瓦解,但“追剧”这一重要的生活方式却依然强势无比。
这些都是走过一个甲子的国剧最鲜活的社会文化倒影,或好或坏,都是它应有的模样。
中国的电视业虽诞生于1958年,取得实质的发展却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在国剧迅速发展的40年里,这一独特的流行文化样式不断定义着大众审美,见证着社会文化变迁,也借由各种各样的方式夯实着它的“国民性”。显而易见,拥有深厚国民基础的中国电视,早已释出了超越媒介本身的价值;曾被亿万人追寻的电视文化,今天的生命力依旧。
与“40年”温情对视
写作《藏在中国电视剧里的40年》(下简称《40年》),本意是想以一种稍显松弛的笔触来记录国剧文化在40年的高速变迁里浓墨重彩的篇章。但在书写的过程中,却意外发现伴随一个“90后”电视研究者的视角深入,这部并不那么严谨的国剧史完成了一次意料之外的观察。
电视剧作为一种流行文化,显然构成了对变化中的社会叙事最直观的镜像,也凝结着一代又一代人具有连续性的集体记忆书写,而这些恰恰是超乎其作为一种文艺创作范畴的意义。
2016年是电视剧《武林外传》开播的第十年。十年间,这部剧从乏人问津到至少触发两代人的共同荧屏记忆,成为与《新白娘子传奇》《还珠格格》比肩的“消暑利器”。而时至今日,它也做起了不尴不尬的大电影,原班人马出没于综艺重现“七侠镇盛况”。相比同福客栈的“江湖”,“看”《武林外传》的情致似乎更成为人们共情的基础;2017年,87版《红楼梦》播出三十年再聚首,那些熟悉又有点陌生的面孔在人民大会堂重现。饰演贾宝玉的欧阳奋强用了剧中一言以表感慨:“今日只作远别重逢,亦未为不可。”许久不见的这场红楼大梦,好像就在眼前。
相比其他的文艺类型,或许并没有太多人愿意将电视剧视作一种稳固的社会文化结构。在普通观众的眼中,电视剧是极致审美的,总有《大明王朝1566》《大宅门》这样的正剧立得住、传得开;又或者是纯粹娱乐的,《康熙微服私访记》里的戏说历史,《还珠格格》里的浪漫解构,《粉红女郎》里的都市言情,有如肥皂剧制造的幻象那般想象性地解决着人们“不可能完成的现实”,营养不多,但常谈常新。
站在“电视的一代”的尾声里,我对电视剧文化的理解会带着些许感怀。“90后”见证了国剧人声鼎沸的高光时刻,却也共同经历了“客厅文化”的式微。电视剧的浮沉,正好回应了这个时代的变迁所形塑的某种“大众文化”特征:今天的国剧,相比上世纪80年代的古典和雅致显得更通俗;相比上世纪90年代的犀利和现实主义也平添了一份无关宏旨的“后现代状况”。若是仅从艺术标准加以审视,电视剧的变化未必惊艳;但在大众审美和流行文化的互相建构之中,电视剧对人们置身的社会生活却有了更为精准、细致的呈现。
这样理解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国剧经典流变,似乎就生成了电视剧更珍贵的阐释——相比其他影视艺术,电视工业的勃兴轨迹创造了“流行”的更多可能性;而电视剧,不仅成为介入我们日常生活的一种文化产品,更是塑造我们社会身份的文化模具。常江博士在为《40年》写的序中提到,“在过去这半个世纪里,没有什么比共同观看过的电视更能界定一代人所共享的世界观,也没有什么比那些虽诞生于某些时代的独特语境之下,却又以记忆烙印的形态经久不衰地存在于社会文化空间中的电视文本更具阐释的意义。”中国电视剧,直观再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审美文化主潮的变迁轨迹。它可能呈现出的去中心化、去深度化的表达,或许在美学上值得再反思,但在投射社会精神风貌更迭的方面,却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经典或流行,都是未曾远去的美丽
正因如此,当我们回望中国电视剧的传统时,更不能仅仅从单一的视角和标准加以研判,面对纷繁社会图景的不断蜕变,电视剧所承载的价值是更为宽阔的。所以,《40年》的写作,是建立在希求实现自我表达的基础上,对历史展开的“温情”阐释——我们当然能够对单一的电视剧文本形成具体的褒扬与批评,但当置身于这一种普遍的流行文化之中,一切业已发生的事情其实都有其语境上的根源,一个事物也不会因为“我不喜欢”就变得没有价值;同理,构成一种文化现象的国剧历史变迁,也具有了完整的社会诠释。
电视剧与社会文化的互相成就,是它作为一种主流文化产品的最终意义所在,而这也在过去40年发展的高歌猛进中尽然显露。
改革开放的大潮带来中国电视的结构化转型。从阶级斗争工具到日常消费媒介的角色转换,让以电视剧为代表的媒介文本成为上世纪80年代思想“启蒙”的重要工具。从1978年播出的单本剧《三家亲》到1981年播出的中国首部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初具规模的电视剧形态,看上去只是迈进了一小步,背后却是时代变革中必然的一大步。而在那之后轰轰烈烈的“名著搬上荧屏”,不仅开创了电视剧艺术的真正探索,也完成了一次印着时代特色的国民集体美学教育——今天看来,有如86版《西游记》的作品未必“精致”,但它们所负载的文化意义却是此后国剧历史中绝无仅有的。
90年代的国剧风云更是壮阔。延续着美学层面的探索,中国电视剧也开始深挖其社会立意。《渴望》《我爱我家》《过把瘾》等作品,都以极其现实主义的笔调书写人生况味——也许我们今天已无法理解更无法推崇刘慧芳那样的悲情女主角,也再不会有《过把瘾》里“爱她就爱个腾云驾雾”的炽热情感,但这些带着痛感的叙述都真切存在于彼时的社会时空中,以最纯粹的方式亲近着大众,成就了电视剧延续至今的“国民基础”。
步入2000年,人们指责电视剧愈发“无关痛痒”,却忽略了这也是消费文明高歌猛进的新历史阶段。最后的“电视一代”长大成人,面对生存与生活多重焦虑的拷问;作为一种重要生活方式的“看电视”,也被赋予了别样的意义。电视剧的图景变得繁杂,偶像剧、玄幻剧等通俗类型作品在不断的解构中渐成主流,人们在置喙国剧乏于意义的同时,它却也为大众社会创造了一种极为理想的休闲方式,以间接的介入纾解着高速运转的水泥森林里包裹的个体迷思——这也就不难理解,并不“高级”的《延禧攻略》为什么能在今天的大众市场中备受青睐,目之所及的地方皆有这一社会货币流通,电视剧显然已经拥有了超越美学的经验和发展动力,反身定义了自身的重要社会价值。
伴随改革开放的时代进程而来的,是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在转型中寻找新的方向、勾勒新的面貌。中国电视剧则是重要的文化标本之一,所有的探索自然无法用简单的二元对立标准加诸价值判断,因为这些经验都构成了不曾远去的美好负载。经典的叙述也好,流行的表达也罢,都可以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中找到阐释的路径,也折射着社会变迁进程里那些真实发生的断面——当完成《40年》的写作后才意识到,每一部看似“无足轻重”的“老国剧”,既构成了“我”,也构成了“我们”所在的社会,如书中序言所说,“完全有资格有恃无恐”。
(责编: 常邦丽)
版权声明:凡注明“来源:中国西藏网”或“中国西藏网文”的所有作品,版权归高原(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任何媒体转载、摘编、引用,须注明来源中国西藏网和署著作者名,否则将追究相关法律责任。